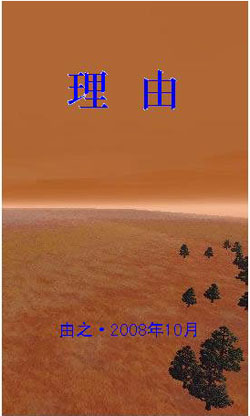碎语《局外人》(发布于2020年08月04日,阅读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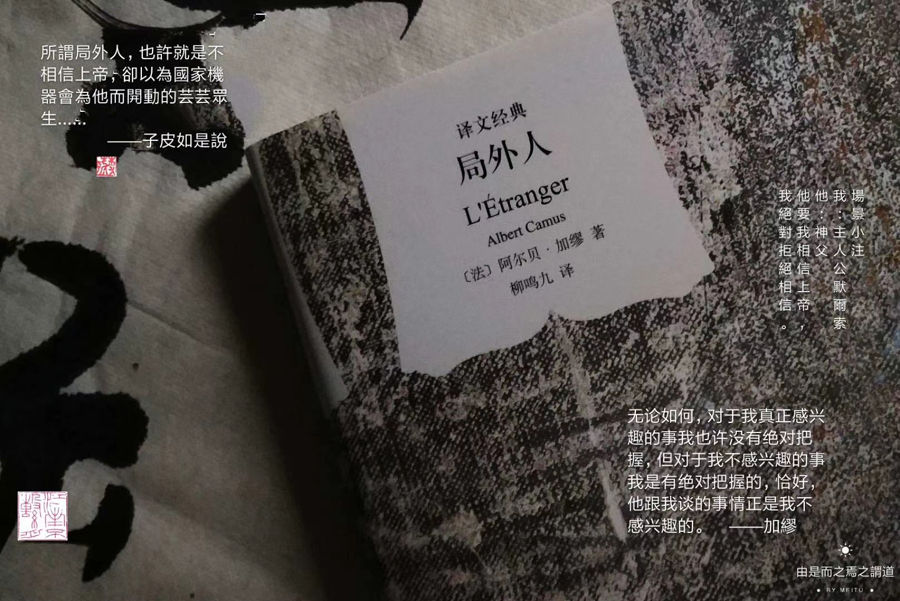
碎语《局外人》
已经忘记最初是什么时候读的《局外人》,印象中应该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品在中国火红的八、九十年代,和世界比较起来至少晚了三、四十年,那时候的我们有点像古代皇帝大赦天下样子,苦囚犯忽然被阳光沐浴的感觉——天窗开了啊。
再读《局外人》,脑袋已经被塞得乱七八糟,中国社会也已经随波逐流到不可思议的浪尖上,而芸芸众生,依旧没逃脱掉局外人的尴尬境地,甚至可能更少去思索这样一个处境。
小说的主题体现在主人公默尔索庭审过程,法官不去追究犯罪过程和事实,而是极尽所能去收集默尔索的个性、人品的“缺陷”,比如把母亲送到养老院,母亲葬礼竟然没流过眼泪,甚至葬礼第二天就和女朋友约会游玩,以此证明默尔索就是一个社会渣滓,然后“以法兰西人民”的民意宣判死刑。柳鸣九说:加缪在《局外人》中没有像雨果一样描写一个冉·阿让,是因为雨果时代可以为了一片包而犯罪,而加缪时代已经不是饥饿问题,而是生存状态问题——精神人格问题。其实,加缪时代也好,雨果时代也罢,小人物总逃避不了“局外人”的命运:国家机器主宰者芸芸众生。象征国家机器的法官,他需要的是形象,判处一个社会“渣滓”死刑无疑会为他的形象增添一份光彩,而是不是应该从犯罪的角度去判处他死刑,此时的法官是不在乎的——小人物的生死在法官眼里,完全微不足道。
那么,已经二十一世纪的现在社会,局外人的命运又如何呢?估计和雨果时代也差不了多少,因为国家机器是没有情感的东西,除非你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或者想成为生产机器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尽可能避免与国家机器产生摩擦,乃是局外人的生存之道吧。可怜的芸芸众生,还热血沸腾地去修正去革命国家机器,祖宗有言: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由之
20200718于上海无乐斋
版权所有:由之中文网 联系youzhi34@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