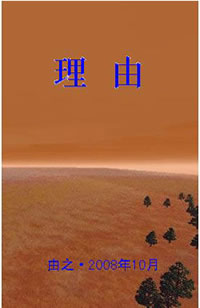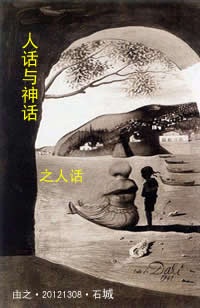篆刻启蒙(发布于2020年10月30日,阅读次)
篆刻启蒙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九州到处是红旗飘飘,大地充满革命激情,学校虽然少了朗朗读书声,但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政治课程天天像模像样地在开课,受“白卷先生”(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某个学校,出现了一个牛逼哄哄的考生交了白卷,被称为革命举动,于是乎学校考试也成了问题)的影响,学校课堂形同虚设,读书无用论弥漫校园,考试一律开卷。假如你想看书,那么古今中外所有的名著统统列为禁书,根本无处可寻。那时候的精神世界真是混沌空虚,单调得如老和尚敲打木鱼,生命如同躺在荒山的石头。课余时间如何打发?像子皮这种没有“天分”的野孩子,也就夏天爬树抓知了,秋天墙角捉蟋蟀,冬天爬高放风筝,春天伏地打弹子。忽一日,发现语文老师在刻印,恍如洪荒宇宙中忽然发现一个目标,顿时勃发了兴趣,时年十五,恰志学之年。
语文老师号“冷斋”,三十左右的年龄,英俊随和,络腮胡子存托出一种西人的男性风度——按照当时上海人的认知,男人的风度就如英国的绅士,有个坚挺鼻梁和“啦大胡子”(上海话,其实也就是络腮胡子)。后来知道,冷斋老师是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上英语课的。那时候学校缺老师,所以冷斋老师兼上语文课。当时和子皮一起跟着冷斋老师学篆刻的,还有一位同学C,他是子皮中学时候相处最好的同学。
初时,不识篆书,冷斋老师说:篆刻篆刻,须以篆书入印。所以每要刻印,就跑到冷斋老师的办公室,由冷斋老师帮着写印稿,然后再用刀。子皮往往会在语文课上刻,一堂课完成一方印的练习,冷斋老师也不来质怪或没收刻印的材料和刻刀。其实,那时还真很少有好学的学生。大抵说来,老师看到学生好学,总是喜欢的。一晃三年,子皮考上大学,结果在大学期间,书法和篆刻得到更多同学的认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子皮担任了上海交大学生书法篆刻协会会长,估计是首任,因为先前还从来没这个团体。
现在回想,启蒙老师冷斋给子皮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其一,冷斋老师告诉了我们学印的印材和刻刀,可以去南京东路的朵云轩购买。始知上海的朵云轩,从此也成为子皮一个免费参观书画篆刻名家的艺术殿堂。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朵云轩的橱窗,橱窗空间小,大作品放不下,所以常会放篆刻作品,而且更换作品的频率也高,会展示名家的印稿和印材,深得子皮喜爱。
其二,入印的字体要统一,初学者尤以《汉印分韵》为主,《缪篆分韵》、《六书通》不足信,显示了冷斋老师的正统性,对子皮影响很大。当时没能力购买工具书,读大学的时候,假如要刻印设计印稿,总要跑到上海图书馆借这些工具书。上海图书馆的工具书是最全的,工具书也不给外借,所以每去一次,总是一早等开门,去晚了可能就会没位置——那时整个社会的读书氛围如蝶恋花,很多禁书还来不及出版,但图书馆已经可以借阅了,比如子皮在哪个时候就看到了许多民国时候的文学作品,包括徐志摩、蒋光慈、闻一多的。上海图书馆的建筑,是旧时的跑马厅大楼,不仅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而且藏书也是最多的,所以最能吸引求知欲旺盛的年轻学子。当时一楼是上海美术馆,子皮参观过好几次欧洲画展,也是初识欧美现代派艺术作品的地方。
其三,大学期间,还和同学C去看过冷斋老师几次,有一次还专门去索字,冷斋老师非常高兴,当场挥毫,为子皮留下了“奇异自然现象”的墨宝,可惜几次搬迁和更换工作单位,墨宝遗失了,甚憾。
顺便补充一下,同学C的父母是小学老师,大学毕业后,其母还介绍子皮在闸北区少年宫开设了篆刻班,第一期,子皮要求学生不能太小,最后报到的十几位学员,最小的七岁,一年级,最大的九岁,四年级。没想到第二期刚开始上课,那个四年级的学生非常高兴地告示子皮,他的作品在区里获奖了……也许是一种欣慰,毕竟,华夏文明的文化艺术不该泯灭。可惜开了四、五期期后,子皮嫌累赘。闸北区少年宫离家很近但离子皮上班的学校相当的远,那时候子皮在学校任教工程力学课程,基本住在学校,所以受不了每周还要去少年宫辅导学生,便结束了课程。
再补充一下,子皮买的第一本工具书是《说文解字》,1981年购买的,1.65元,按印张算,这本书极贵,那时候一印张大概就三四分吧,子皮那时候月入21.5元,也算是爱之切吧。
一晃子皮已经耳顺,时时也会想起冷斋老师,更想约了同学C再一去看看冷斋老师,相信耄耋之年的冷斋老师见到我们一定会相当的开心吧。
由之
20201024于海上无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