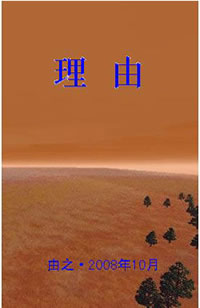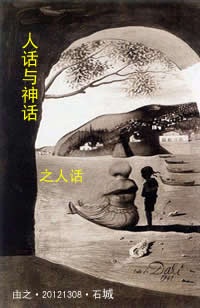偶 然(发布于2007年08月15日,阅读次)
偶 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海,十六浦码头,灯火昏暗的候船厅,大厅用铁拦杆划分成长长的区间,每个区间再安放了两排长长的木椅,每排木椅又长长地坐满了很是木纳昏暗的人们。我紧靠着我的母亲,挤坐在过道堆满行李杂物长椅挤满很是木纳昏暗的人们中间,耳边是母亲不停地叮嘱——我,十四岁,正值暑假之际,将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坐船去南通,然后转乘长途去大丰,我母亲的第二故乡,有我的舅舅姨妈姐姐弟弟妹妹们。一阵骚动,整个候船大厅的人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个一个区间的放行,母亲被阻挡在进口处,而我背着书包手提旅行袋随着人流匆匆走向靠在码头的轮船,母亲的叮嘱渐渐离我远去。
第二天清晨,当轮船靠上码头后,你可以看到浩浩荡荡的人流犹如冲向某个战略要点的军队,当我被人流带到长途汽车站时,我被更混乱的人群所淹没,虽然车站指示牌高高在上,只有
每当我想起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远门就被人骗的时候,我纳闷:为什么我没有仇恨陌生人,没有诅咒社会?答案是,因为我天真。在我挤上长途汽车后,只有门口一小块地方刚好让我坐下,尘土飞扬喇叭高叫已无法让我停止思绪几个小时以后看到我舅舅时的情景。我遇到的只是一个偶然,一个错误,能够补救的错误都算不了什么错误,就看你有没有去努力。至于那个叔叔,那个拿了我两毛钱的叔叔,也许还会再拿别人的两毛钱,当然也许他需要,当然也实在只是一个偶然,随着一站站靠近我的目的地,我激动无限,那个叔叔的影子早抛到车轮后面无影无子踪了。
假如人人都能遇到这个偶然,也许有人会仇恨,有人会诅咒,甚至还会被腐蚀,但我相信,假如人人都在提防,假如人人都在怀疑,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
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