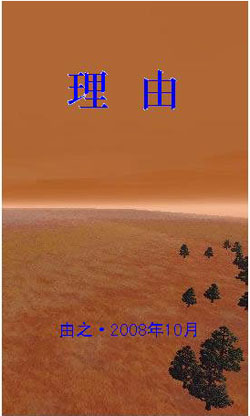《诉讼笔录》(发布于2008年10月02日,阅读次)
《诉讼笔录》
〈法〉勒·克莱齐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第二次印刷。
“你觉得在等待着什么东西,恩?某种令人生厌的东西,或者某种与其说危险,不如说讨厌的东西?——是这样吗?你感觉到在等着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那好。听着。我就告诉你。我也一样。我也感到在等待。可好好理解我吧:我呀,要是我还没有确信这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就要临头……或迟早有一天必定要临头,我对这种等待的感觉就根本不在乎。这样一来,说到底,我现在就再也不等着任何讨厌的东西,而是等着某种危险的东西。你明白吗?这纯粹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方式。要是你跟我说出了你没有告诉我的东西,比如,跟我说你感到在等待着什么东西,说你知道了,明白了,你知道那可能就是死,那么,这就O·K。我就理解了你。因为说人在等死,这最终总有一天会显出其道理来的。可是,你明白,是不是,重要的不是你拥有的那种不快的感觉,而是无时不刻在等待着死亡这一事实,不管是有意识地等,还是无意识。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你知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某种生命系统中,人们只要存在,就无不在实施这一系统,你也就留下了消极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讲,它完满地完成了人类的统一。……” P57-58
“这就是说,在辨证——从这一角度看,说辩术更为贴切——推理系统中,对,在这一不涉及经验的推理系统中,只要你对我说一句:‘Quelle heure est-il?’(意为现在几点了?)我就可作出解释:Quelle,为特征疑问,源自一种错误的宇宙观,按照这一宇宙观,一切均被分门别类,人们可以像从抽屉里取东西一样,从中挑选适合某物体的特征说明。Heure,时间,抽象概念,可分为分与秒,若添上无限次,即产生另一个抽象概念,叫永恒。换言之,时间包含有限与无限,可数与不可数;两者矛盾,因此,按照逻辑观点,为无意义。
“est?存在:这又是一个词,是与抽象相比较的一种拟人说,如果说存在就是一个人的联觉的总和的话。Il?同属一类。Il,并不存在。Il是阳性概念在时间这一抽象概念上的普及使用,此外还用于一种不规则的语法形式,即无人称,与est这玩艺儿联在一起使用。等等。整个句子都与时间有关。就这样。Quelle heure est-il(现在几点了)?Quelle heure est-il?这个小小的句子,要是你知道它多折磨我!或者说不是这样,是我自己受它的折磨。我被自我意识的重负压扁了,这是事实,米歇尔。这害死了我。可万幸的是,人们并不是按照逻辑生活。生活不逻辑,它也许就像某种意识的无规律现象。一种细胞疾病。这无关紧要,不成其为什么理由。……” P59-60
“是的,现在几点了?”
“现在的时间是,夜色明亮,动荡的大地周围,星光闪闪……” P61
就是在那个时期,他有所领悟,发现人们双肘紧贴身子,目光倔强,大都无所事事,在闲极无聊中打发时光。十五岁那年,他就知道,人都看不透彻,都不诚实,他们每天除了完成那三四件遗传性的事情之外,就是在城里走呀跑呀,想不到可以到乡村去,让人给自己建造千百万座小屋,在里面生病,想入非非,或者懒洋洋地过日子。 P89~90
随便举一件事为例吧,比如抽一支烟,关键在于要在同一个动作中无限地感受到地球上另有千百万人可能同时在抽另千百万支香烟。感受到千百万支轻轻的圆柱形纸烟伸进唇间,吸进几克交织着烟草味的空气,这样一来,抽烟的动作便成为统一的了。它形成一个种类;宇宙起源论和神话论的习惯机制便可以起到作用。 P191
我每天的时间这样打发:我拥有一块田地,地里尽是石头,从早到晚都有阳光。在地中间,我生上火。找到什么就烧什么,木版啦,玻璃啦,生铁啦,橡胶啦。就这样,我直接用火制作一些类似雕刻的东西。一些在风中,在尘土中烧得焦焦的、漆黑的东西。我往火堆里扔些树干,将它们烧掉;我把一切全都拧弯,全都烧黑,全都涂上一层吱吱作响的粉末,让火苗直往上窜,腾起浓浓黑烟,落下沉沉的涡状烟灰。橙色的火舌布满地面,震撼天空,云彩。苍白的太阳与火舌进行数小时的激战。…… P198
在城里,人居住的有两种不同的房子:一种是住房,另一种是疯人院。疯人院里房子也分两类:一类是关疯人的,一类是夜晚收容所。夜晚收容所里,只分为给富人住的房子和给穷人住的房子。给富人住的是单间,收留穷人的,是集体宿舍。集体宿舍里,尽是便宜的和不值钱的玩艺儿。在不值钱的玩艺儿中,有救世军。对救世军,大家并不总是很买帐。 P212
讲话轻而易举,最令人厌恶的,莫过于听人当面讲故事。听人信口编造。然而你们却习惯了。你们不是人,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P232
这很简单。只需要了解三点。响尾蛇。很傲气。不喜欢爵士乐。一看见火绒草,就犯蜡屈症。那么。应该这样下手。您拿起一支单簧管。您见到蛇时,给它扮鬼脸。既然它们很傲气,它们便会发怒,朝您冲来。这时。您就冲着它们演奏《蓝色的月亮》或《纯粹是个舞男》。用单簧管吹。它们不喜欢爵士乐。这样,它们便会停下来。犹豫不决。就在这时,您掏出来。您从口袋掏出一朵真正的雪地里生长的火绒草。它们马上就会犯蜡屈症。这时,只需要招手去抓,并对着它们身上的某个部位轻轻地哈气。待它们醒过来。它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复存在。不再是什么响尾蛇。由于它们傲得可怕,准会受不了。它们宁愿自杀。于是,便屏住呼吸。一憋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它们自己憋死为止。成了黑乎乎的一团。 P237
还有床:他经常想,等以后有了钱,一定要给自己的床按上轮子,推到外面去。尽管知道外面天气冷,他也会感到热,钻到被窝里,同时与外界保持直接的联系,这房子那么窄,那么闷,致使他对自己的想法确信无疑。也许,他想做的首先是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他极少碰到,差不多从未有过。他坚信,如果躺在那里睡觉,那他就用不着在深更半夜悄悄地回到床上去,环顾四周,设法弄清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凭自己大脑的想象,猜想这儿是个空大衣架,那儿是一把椅子和一条毛巾,更远处,是美丽的月亮投射的窗条影,等等。如若那样,他也再也不用在上床睡觉前记住各种东西放置的位置,再也不用脑袋冲着房门的那一侧,以有所戒备。 P244
“很好。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山上也很好。可以看到山下的公路。我光着身子晒太阳。”
“您喜欢这样?”
“对”
“您不喜欢穿衣服?”
“天气一热,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穿衣服要扣扣子。我不喜欢口子。”
“那您父母呢?”
“我离开了他们。”
“您是出走的?” P259
“一般说来,孩子都比较愿意跟别人在一起,”戴黑眼镜的小伙子说道。
“要是您愿意这么说,那是的——是的,这不错,他们都比较愿意跟别人在一起。可同时,他们也在寻找某种——怎么说呢?——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我觉得——他们都乐意——他们很容易顺从于某种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化的——需要。可也在寻找一种渗透到事物中去的方法,因为他们也很惧怕自己的个性。事情的发展,就好象他们的父母给予了他们一种自我贬低的欲望。他们的父母使孩子们物化——把孩子们当作可支……的物品——当作可占有的物品。他们给孩子培养了这种物化心理。这样一来,就导致了这些孩子惧怕社会,惧怕大人的社会,因为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彼此是同等的。正是这种同等使他们感到惧怕。他们必须担当某个角色。人们期待着他们做某种事情。于是,他们宁愿打退堂鼓。他们在寻求一种方式,以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拥有一个有点儿——点儿神秘的天地,一个玩耍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们与无活力的物质并存。或更确切地说,他们能在这个天地里感到自己是最强者。对,他们乐意感到自己与任何东西都是平等的。他们甚至走上极端,改变自己的角色,而自己则扮演大人角色。你们明白,在一个孩子眼里,一只马铃薯甲虫,与其说是另一个孩子,不如说是一个大人。” P261-262
“您做过什么中意的工作?”
“小事,我都中意。”
“什么小事?”
“呃,冲洗汽车,比如。”
“可您——”
“海滨浴场值勤,我也高兴。可我出来就不会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想当通烟囱的,掘墓的或开大卡车的。得要有人介绍。”
“您想一辈子都做这些事?”
“为什么不行?掘墓的,可有不少老手,您知道的……” P267-268
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