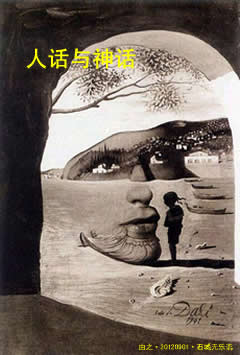游戏文字只是因为社会万象给了文字游戏的机会,一如水中之月,是因为夜晚的神秘,生出了诗话的趣味……
——由之
非议《三峡好人》(发布于2007年10月18日,阅读次)
非议《三峡好人》
一直不敢看国人导演的电影,是因为担心我的心情承受不了悲哀和叹息。从张艺谋走向末路后,几乎就没有看过什么国人导演的电影,看张艺谋最后一部片子是《秋菊打官司》,我就想,他已走向穷途。当张艺谋用天文数字的人民币打造的大片铺天盖地地砸向商业主宰的娱乐社会时,张艺谋的脸上充满了阳光般的笑容,从此,他不再是个艺术家,不再追求艺术的含义甚至价值观开始紊乱。
即便如此,还是忍不住在十一黄金周观看了今年在狮城获奖的影片《三峡好人》,凄凉至极!有人心平气和地说,从头到尾,只是把《三峡好人》当作记录片来看的。贾樟柯说自己做的是文艺片,很是纳闷。所谓文艺当然是要有文学或者文化和艺术性,一部充满符号臆想的片子,像在游戏电影,拼凑各种主观的零碎的场景,把电影艺术的魅力丢失殆尽。
首先是主题严重丢失。《三峡好人》的主题是什么?很多人看了以后不知道贾樟柯要说的好人是谁,男主人公不是三峡人,女主人公也不是三峡人。导演想说的也许是:三峡人真好,政府一声令下,便一拨一拨的三峡人离乡背井,是老实人和老好人,很是反讽。然而除了拆迁和离开三峡的客轮以外,看不到贾樟柯反映主题的线索。很难想象导演的能力,一个如此巨大的迁移,竟然用如此平淡的画面、人物、与主题几无关联的剧情串在一起,这是当代导演的一种才气?国人有一个极为虚弱的情怀,只要在国际上获得什么奖项,那一定会好评如潮,这让我想起原始部落的游民高举火把的愚昧疯狂景象,国人的电影人真是可怜。按理说,地球人是智慧动物,而国人更是充满文明智慧的人种,为什么会因为老外的一个带有明显偏颇的评价便欣喜若狂?任何作品只要一贴上人性的标签,一定身价飚升,价值无限,倒很想问一问导演贾樟柯,《三峡好人》的人性反映在哪儿?据说,西方有人评价中国的电影很弱智,所以,我就想,也许弱智到了一定的境界也可以获得奖赏吧。
艺术来自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是简单的常识,假如不能提炼升华,假如没有加工创造,假如缺乏艺术灵感和艺术悟性,那就只有平庸,那是“工匠”的劳动而不是艺术家的创作。《三峡好人》给人的感觉是像在做一个电视节目,实地抓拍,简单剪辑,加上导演的一些主观臆想,算是拼凑了一部“作品”。韩三明在表演在演戏吗?两条主线是在说合法的婚姻最终走向末路而不合法的却走向希望?什么飞碟啦走钢丝啦好好的建筑忽然像火箭一样升起啦零零碎碎的雕虫小技,据说隐含了导演的良苦用心,疑惑导演究竟想说什么。电影是一个叙事、表演功能很强的艺术,它不是小说诗歌散文,那么多与主题毫无关联的符号、画面,作为只知道看电影的我们来说,心如死灰。我们总不能随机地把夜排挡的吆喝看成是艺术,我们怎么想象一个小女孩在江边逢人便说要不要保姆这样的画面,与导演这部电影的精神联系起来呢?鲁迅曾经说过,一个画家是不能把一泡屎或者臭虫之类的东西画进画面里的。所以,对导演自称为文艺片的《三峡好人》,只能理解为贾樟柯重新定义了所谓的“文艺片”。
还想说的是,电影的戏剧效果。《三峡好人》的电影中,看不到冲突(这是戏剧起码的因素),没有震撼感(这是显示人性的必然结果),而且几乎没有愉悦的因子。这让我想起储安平的语调:“一场烂污”!这年头,老老实实做事的人确实少而有少,问题是,艺术不是你随心所欲想当然的那个东西,不是巧取投机就可达到你想要的那个境界。艺术这个东西,确实需要很大的天分,不是所有的人想玩就可以玩的。当然假如你躲在自己的小屋做给自己看,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而丢人现眼就不太有趣了。
由之
2007年10月